6月7日《科学时报》低碳能源双周刊上发表了三篇有关秸秆直燃发电的文章,文中对该报5月24日发表的《一座生物质电厂的账本》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文是该报记者李晓明对我的访谈。
对我国能源问题开展公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能源及其相应的环境问题对我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大家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有了讨论、交流就可以拓宽视角,得到较为合理的看法。这三篇文章我都仔细地拜读了,受益匪浅。因为《一座生物质电厂的账本》一文是记者对我的访谈,记者没有问到的问题我也没有详细加以解释,确实有不明确之处。所以试图通过这篇短文对其中一些数据的采用,以及把我国秸秆的利用放在一个中国农村、农民能源系统优化的角度作一些诠释。
我国能源的需求和供应已进入多样化阶段,煤、石油、天然气、核、可再次生产的能源都将成为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和农村的能源服务的需求也一直增长。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中央、地方政府部门首先要考虑的是从系统高度对各种能源所能发挥的作用作出合理定位,使其得到最优化的利用,不能“各打各的仗、各吹各的号”。我个人近年来形成的一个明确的看法是:把合适的能源用在合适的地方,分散能源(如秸秆等)分散利用,集中能源(如煤、油、气、核等)集中转化,用已形成的基础设施(电网、气网、热网等)输送至终端用户,朝这个方向努力,能源系统就能够达到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
秸秆类生物质怎么利用一直是我考虑的问题,人类已逐渐进入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越来越广泛利用的时代,人与自然的交互越来越频繁(化石能源是太阳能数千万、数亿年的沉淀,而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是当年的太阳能),因此,对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生产和应用也应十分谨慎和小心,否则,将会引起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以及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实际上这类问题已发生了)。
秸秆直燃发电是将生物质转化为电,我认为在中国普遍推广是不合适的,但是在一些秸秆资源比较丰富、集中的地方仍不失为一种利用方式。在访谈中我也指出,如一些沙棘平茬复壮地区、需要工业供热地区、可以混烧地区
但据我所知,有一些地方,不顾实际资源情况和其他能源的供应情况,一下子规划了很多秸秆直燃电站,实际上又建不起来,就是一个教训。此外,随技术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秸秆更好的用途会慢慢的多:如可用来生产沼气(不是户用型的沼气池,而是和养殖场相结合的中大型沼气池,在北方由于全年温度较低,正在研究更好的生物降解方法,沼气、沼废料都有使用价值),沤烂了以后还田(我国长期施用化肥,导致土地板结、元素失衡),颗粒化并配以方便、廉价的炉子用于炊事和采暖,以及可用作地方工业的原料都可以因地制宜加以考虑。
由于上述利用方式的采用,在一个给定地区可收集的、用于直燃发电的秸秆将会慢慢的少。单县供24MW的电厂需秸秆20万吨/年,收集面积是1800平方公里,恐将来这个电厂所需收集面积还会随原料的供应情况扩大(原料的供应情况出现变化)。理论上收集的运输距离和收集面积是平方根的关系(即收集面积增加一倍,运输距离增加倍)。
我国一次能源多煤少油。从长远看,煤作为一次能源的比例仍将占50%左右,绝对量大约是30亿吨标准煤/年,这些煤将来有70%以上用于发电,目前这一比例约占52%。煤的高效清洁利用只能在大容量、高参数的蒸汽电站或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以及多联产系统中实现,必要时还可加上适当的碳捕集、利用和埋存系统(CCS、CCUS),这就是目前和将来我国煤的主要利用方向。目前我国已有不少的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它们每发一度电的CO2排放大概是0.7~0.75kg。我国的煤矿也正在加大整合力度,提高生产安全性和效率,如淮南煤矿全员生产率是6吨/(人天)。油是我国相对稀缺的资源,目前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2%,且不断增大,构成一定的能源安全问题,为解决这一个矛盾,我国正在发展作为液体燃料的石油替代技术。煤直接和间接制油是其中之一。
因此,消耗什么样的资源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考虑到其稀缺性。这也就是我在访谈文章中使用先进发电数据(0.7~0.75kgCO2/kWh)和对运输秸秆所消耗的汽柴油折算成煤制油及相应CO2排放的理由。
秸秆本来是很好的资源,只是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政策、技术、管理不到位,形成野烧现象。而直燃发电就是把这部分原来“无用的、扔掉的”能源变成有用的。
如何解决农户供能问题?不论从过去传统和将来来看,秸秆仍是农民用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人均耕地少,这部分秸秆除饲料、还田等用途外,用作燃料的使用量是有限的,有时还不得不用煤、液化石油气等其他能源作一些补充。不管怎样,这部分秸秆能源应该通过政策、技术、管理把它用起来,纳入到农户用能的范畴。所以,秸秆的利用必须和农户用能、给农民提供现代化的能源服务,以及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集合起来。
因此,从“直燃发电农户”用能总系统来看,农民把秸秆出售给电厂,所出售的“热值”,必然要有其他同等“热值”的燃料来补充,譬如说煤。这几年来,农村用煤量增加不少,而农村中烧煤肯定要比大电厂的效率低、污染高。农村采取对应技术把多余秸秆就地利用好,可以使“直燃发电农户”用能总系统优化,这是前面提出的原则“把合适的能源放在合适的地方”的体现。因而,把出售的热值用煤补充来计算CO2排放是合理的。这是“直燃发电农户”系统排放CO2的主要部分。在访谈文中提到,1吨秸秆的热值(3500大卡/kg秸秆)相当于半吨煤(7000大卡/kg标准煤),这半吨煤直接燃烧可排放1200kgCO2。
秸秆的运输不同于其他大容重的货物运输(容重单位体积的重量),用平均货物运输吨公里(1吨公里1吨货物运输1公里)来算油耗是不合理的。秸秆的容重很小,一般自然态是12~20kg/m3,初步打包是25~50kg/m3,若先铡成小段后运输则是70~100kg/m3(1吨要额外耗费20kWh的电用于铡段),这样1吨秸秆的容积大概是10~20(30)m3,体积是很大的。由于我国农村是小农经济,不可能用大规模机械化高密度打包。因而,一辆拖拉机加正规的拖斗,或一辆农用车所能装载的秸秆重量是有限的,与装大容重货物很不一样。所以,每吨秸秆运输所耗的油可能和真实的情况有些出入,但这部分CO2排放在计算中不起主要作用。
1.“国能生物发电集团,秸秆直燃装机容量40万kW,几年来供电累计52亿kWh,燃用了秸秆700万吨”。从以上数据得出,每kWh用秸秆1.346kg,若以3500大卡/kg的热值计算,则供电热效率低于20%。国外先进的秸秆发电电厂的热效率为29%~30%。到目前为止,任何先进热机都不可能达到80%的热效率,热电联产的热效率也很难做到97%。
2.“农民收入19亿,共计用700万吨秸秆”。农民收入折合到每吨秸秆为19×108/(700×104)=270元/吨。估计每户农民可出售的秸秆也就1吨左右,若他们要花钱买同热值的煤,也就抵消了这部分收入,惠农效果实际有限。
3.“国能生物质发电52亿kWh”,若每kWh国家补贴0.35元,则52亿kWh可得国家补贴52×108×0.35=18.2亿元。农民收入19亿元和国家补贴相当,也就是说农民所得增收基本相当于国家补贴,这笔账该怎么算?
4.“这40万kW的电站,给农民创造了5万个工作岗位”。我不清楚这里指的工作岗位是什么含义,若是5万个全时工作岗位,则国能公司的总量40万kW的电站除了本身的职工外,还要有5万人为之场外服务,比“现代化大电厂+煤矿开采+运输”要多好几十倍。从发展角度看,这种就业是不可持续的,不符合新农村建设规划的要求,农村劳动力应该创造更大的价值。
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是新生事物,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扶植,因而,在发展的前期国家给予适当补贴,让其更快地成长起来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要明确,现在的补贴,目的是将来不补贴。
从长远来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一定要不断减少相关成本,自身在经济上可行。例如,太阳能光伏发电虽然目前成本比较高,但从科技发展角度,在成本下降方面有较大潜力。而对于秸秆直燃发电,似乎成本下降潜力不大,它具有先天性的缺陷:一是机组功率小,蒸汽参数低,热效率提高潜力小;二是中国是小农经济,秸秆收集困难,同时,在一个地区,秸秆还有多种利用方式,更加增大了收集半径,要耗费更多劳动力和较高运输成本。所以,不具备未来成本下降的空间,不得不长期依靠补贴,这是发展的一大障碍。
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一个秸秆直燃发电厂是否能达到像大电站那样的运行寿命(30年以上)?且不说这类电站每kW的基本建设费用是目前先进大电站的2倍,它们的“存活期”会有多少年?(并不是设备老化,而是外界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原料供应情况的变化。)这样,建设能耗和基本建设资金分摊到单位发电量上肯定比较高,即从全生命周期来看每度电的成本和CO2排放会较高,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归纳一下,从系统高度来分析各种能源的优化利用,把合适的能源放在合适的地方;考虑到全生命周期和新农村的能源供给是我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意见希望相关的同志,尤其是政府的能源管理部门商榷、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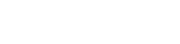






 2025.04.09
2025.04.09







